在《電影作為檔案》 (2011) 一書中, 筆者較系統地論述過紀錄片與文獻紀錄片概念, 并計劃對紀錄片理論做一次全面梳理。然而此后在對口述歷史紀錄影像與紀錄片的論述中, 赫然發現諸多本以為已解決并需以此為基礎進一步發展的基本問題, 仍在國內主要學術刊物上處于混亂狀態。
筆者的思考顯然沒能引起紀錄電影學界足夠的關注, 原因估計是少有人認為該書跟紀錄電影乃至電影學基礎理論的開拓有關, 因為諷刺的是, 也有不少沒能認真閱讀的檔案學者反過來認為該書基本上是一部電影學著作而與檔案學關系不大。盡管在電影理論中引入檔案學的理論或反之并非筆者首創, 國際上也非偏僻, 甚至國內主要電影學術刊物上也有過相關譯文, 1但對絕大多數國內電影研究者來說還是個陌生的領域。這種陌生其實也說明了本文乃至《電影作為檔案》想要說明的問題。
因此, 哪怕是為了順利推展口述歷史紀錄理論, 筆者也不得不改變計劃, 回頭對一些紀錄電影的基本問題提前展開論述。其中文獻紀錄片是矛盾比較集中的概念。正如《電影作為檔案》一書中所提到的, 國內特有的電影藝術檔案概念雖然走向了另一個方向, 卻成為一個絕好的例子來明晰地說明和暴露國際上電影檔案概念中所存在的諸多模糊認識, 文獻紀錄片也是如此。筆者曾提到, 文獻紀錄片是個土生土長的中國術語乃至概念, 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人對紀錄電影概念的某種認識, 對這個概念的分析也能部分地將這種認識揭示出來。
一、說過的話
《電影作為檔案》第六章第二節《電影檔案編纂與文獻紀錄片》曾有過系統的邏輯分析, 2本文不予重復而僅是進行歷史分析, 但作為論述基礎的紀錄電影乃至紀錄理論卻散見全書, 故有必要對書中相關結論做一個簡要概括, 便于讀者理解。
文獻紀錄片作為本土術語, 一個理由是其在其他語言中, 特別是紀錄片概念形成的英語中幾乎找不到類似表達, 因為紀錄片 (Documentary) 這個詞最妥當的直譯就是文獻片或檔案片。3正如很多學者所認識到的那樣, 紀錄片是具有文獻價值或基于文獻制作而成的電影, 4那么文獻紀錄片反過來直譯成英語就成了“Documentary Documentary” (文獻文獻片) , 荒謬性是顯見的。筆者對電影片種的區分是以制作目的所形成的特有文本形態為主要依據, 紀錄片是以制作文獻或檔案為基本目的并具有一定傳播目的的影片為核心、外延逐層擴展的開放式片種類型。文獻性是紀錄片的基本屬性, 更不用說具有文獻價值。
用“文獻”修飾“紀錄片”, 并將其確定為紀錄片中的一種類型, 至少有三種可能的理解:具有文獻價值或文獻性的紀錄片, 關于文獻的紀錄片以及基于文獻制作的紀錄片。目前學術界較為主流的看法是第三種, 即將這個概念與西方“匯編電影” (compilation film, 筆者改譯為編纂電影) 等同。這種等同是存在問題的。首先, 文獻紀錄片并不限于匯編電影的外延, 因為文獻紀錄片概念中所基于的文獻不僅是資料影片, 也包括其他類型文獻:紙質檔案、歷史論著、歷史遺跡與文物等, 而后者在西方關于匯編電影的諸多論述中基本不存在。其次, 匯編電影概念本身的外延也遠超紀錄片, 它可指日本動畫連續劇的縮編電影版;可以指虛構電影片段匯編, 如演員的演藝廣告乃至匯編故事片片段的惡搞視頻如《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甚至完全虛構的基于影像匯編情節形成的故事片如《女巫布萊爾》等。在西方諸多關于匯編電影的論述中, 筆者總結了那些與紀錄電影直接相關的部分論述中兩個主要的觀點, 即理查德·巴薩姆 (Richard M.Barsam) 的“……始于剪輯臺, 使用以前出于其他目的制作的電影膠片”。5以及陳力 (Jay Leyda) 的先決條件——“思想, 因為按照這一形式制作的大多數影片都不滿足于僅僅是作為記錄 (records) 或文獻 (documents) ”。6
盡管由于約定俗成以及文獻紀錄片樣式確有研究價值等原因, 我們仍可采用這一概念, 但從概念誤用中可看出, 我們對一些紀錄片基本概念的認知混亂。筆者也的確提到, 文獻紀錄片最初的含義是上述三種可能含義中的第一種, 即具有文獻價值或文獻性的電影, 但仍是一種誤用, 可引發有價值的思考。本文希望通過有限的考證基本確定這一誤用的判斷, 盡管仍需學術界進一步挖掘。文中盡可能基于影片當時的自我稱謂 (影片內或影片宣傳材料、腳本等輔助文字材料等) 以及當時文字媒體上對影片所做的描述性語詞。限于篇幅, 如有一部影片被諸多報道稱為文獻紀錄片, 本文通常僅舉一例。
二、早期電影與“文獻”的關聯及蘇聯影響
筆者曾提到, 第一個明確將文獻紀錄片與匯編性紀錄片建立關聯的是中央電視臺的時間。他認為“文獻紀錄片的叫法源于《大型文獻紀錄片——毛澤東》 (1993年出品, 中央電視臺與中央文獻研究室聯合攝制) ”。7他談到的是電視紀錄片, 但文獻紀錄片“這個叫法”在電影界卻很早就出現并大量使用了。筆者曾追溯到最早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的中蘇合拍紀錄片《中國人民的勝利》, 而第一部采用文獻紀錄片的純中國電影是《抗美援朝》 (第一部) 。經過筆者進一步搜尋, 無論是影片片頭及其宣傳還是媒體報道, 仍然沒有找到更早的案例。這兩部影片都與經典的匯編電影定義相去甚遠, 理由不再贅述, 至少它們不是經由資料影片匯編而成。在此之前, 中國共產黨電影機構拍攝的幾部比較類似的較長紀錄片, 如《富饒的東北》《百萬雄師下江南》 (甚至還“匯編”了上海影人拍攝的解放前上海的影片素材) 都沒有文獻紀錄片的描述, 而同樣涉及一定歷史性回溯的《東北三年解放戰爭》的描述詞是“歷史紀錄片”。
文獻紀錄片語詞的產生原因, 筆者對那個時期曾留蘇的紀錄片剪輯師姜云川有過電話采訪。他個人認為該詞源于蘇聯, 因當時蘇聯的紀錄電影制片廠被翻譯為“蘇聯中央文獻電影制片廠”, 而這個“文獻電影”意味著這樣的影片可作為歷史資料?,F在筆者找到了更多材料佐證這一判斷。
漢語中, 紀錄片 (記錄片) 這個語詞的用法始于20世紀30年代, 到40年代已有較廣泛地使用,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最終確定下來。在此期間, 無論人們對紀錄片內涵有什么看法, 實際有過多種術語, 這方面筆者將另文詳述。文獻電影或文獻片是這些語詞中的一部分, 卻極為少用, 并在很晚才開始。漢語文獻中, 文獻與電影的關聯也不算少, 但早期基本上是關于電影媒介自身的史料或歷史陳述, 而電影作為史料或文獻并未被意識到。影片本身作為文獻的觀念首先是金陵大學理學院的電教刊物《電影與播音》在1943—1945年間從電影教育的觀念出發, 將電影視為一種類比于紙質書刊的影音版教學材料, 分別采用過“電教文獻”8、“電影文獻”9和“影音文獻”10等稱謂, 并且部分建立在金陵大學的圖書館影音材料收藏, 或電影教育材料制作與專業課程名稱的語境之中, 甚至試著用圖書分類的原則對電影進行各門學科的分類, 而不是僅將其歸入藝術作品類, 與圖書館將所有收藏稱為“文獻”類同。這正好說明了文獻概念的復雜性, 也是很多紀錄電影研究者的困惑之源, 也因此“文獻”概念不能簡單化地用于作為片種的紀錄片的區別標準, 即紀錄片應該是以文獻為基本的制作目的而非出于其他目的制作完成后被視為文獻。
筆者找到的最早相關紀錄片的“文獻”案例, 是1947年一篇關于“中制”與美技師合作完成《中國的抗戰》的報道, 提到該片“是綜合中國二十年來的史料完成”, 11稱之為“中國第一部文獻片”。這部影片的確讓我們聯想到匯編電影, 但“中國第一部”的表述似乎又將歷史上類似的《國民革命軍海陸空大戰記》或《勛業千秋》排除在了文獻片之外 (當然也存在作者不知道這兩部影片的可能性, 盡管這種可能性不大) 。雖然作者沒有明確表述何謂文獻片, 但可以感覺到應該與“史料”匯編以及作為“史料保存”都可能有關, 因為文章最后評價影片“實為中國第一部現代文獻片”, 或也可理解為將這些零散材料匯編形成文獻, 而這些零散材料當然是有一定時間間隔的影片資料??紤]到資料影片長期不被國人視為文獻范疇, 我們更偏向于認為, 此文的一大貢獻是較早認識到電影作為史料意義上的文獻屬性, 但似乎并沒有意識到現時的紀錄片本身也可以以文獻為目的。這一匯編電影樣式的標簽卻不是文獻紀錄片, 而是可以回譯為“紀錄片”的“文獻片”。在紀錄片術語已大量使用的情況下, 這一稱謂也表明作者并不認同紀錄片具有文獻性從而需要另尋一個語詞并加上“中國第一”的描述。事實上, 在今天很多文章中, 文獻紀錄片也常被稱為“文獻片”。
如果說上例還能跟匯編電影聯系起來, 并且沒有蘇聯的影響, 那么接下來不多的文獻片語詞的使用就幾乎總是與蘇聯有關了。例如1948年年中, 《申報》刊登的蘇聯“五一”節大檢閱紀錄片的兩份廣告中, 分別用了“文獻片”和“文獻影片”的標簽, 而這部影片明顯與匯編電影概念無關。對照一下文中對影片出品機構的翻譯, 或許能明白這一表述的原因:“莫斯科檢閱文獻影片·全部五彩·華語解說蘇聯文獻電影廠制”。12這個廠就是前述姜云川提到的“蘇聯中央文獻電影制片廠”。不過, 該廠的名稱Центральнаястудия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хфильмов, ЦСДФ對應的英文名稱正是“Central Studio for Documentary Film”, 所用的詞正是格里爾遜紀錄電影所用的“Documentary”, 但在這里卻被譯為文獻電影而不是紀錄電影。
無獨有偶, 在解放區, 《人民日報》1949年5月關于蘇聯文化近況的兩篇新聞報道中, 也對蘇聯紀錄片采用了“文獻片”的用法:“記載莫斯科今年慶祝五一節盛況的新文獻片《五一節》, 已于五月十六日在莫斯科獻映。該片系文獻片中央制片廠出品。”13制片廠的名稱不同于上述的例子, 說明這一翻譯還沒有定型, 卻仍然將紀錄片翻譯為文獻片。這部影片應該說仍然與匯編電影的樣式無關。
既然只有文獻片的表述而不是文獻紀錄片, 就暫時還沒有產生概念上的混亂, 或者也可以隱約地表明了紀錄電影進入中國的初期階段人們對紀錄電影屬性的不同認識, 使用那些不同語詞的人或許自身也沒有意識到他們其實表述的是同一個所指。對于“文獻片”的使用者來說, 今天已難以考證其術語使用中的真實想法, 僅推測這一時期“文獻”在類似語境中的使用含義。無論是關于電影的史料, 還是《中國的抗戰》使用史料的匯編, 在一般電影人或媒體人眼中, 文獻與“史料”是具有密切相關性的。這也印證了姜云川對筆者的表述, 即“文獻電影”意味著這樣的影片可作為歷史資料, 無論是根據史料影片匯編而成, 還是當下拍攝下來可作為史料的影片, 如蘇聯的五一節慶祝盛況等, 從而與是否是資料影片的匯編無關。更有甚者, 文獻電影這時還可能被用來指某種歷史題材的故事片, 如1949年底《大公報》載一篇譯自俄文的文章14提到了“文獻電影《列寧在十月》”這樣一部著名的故事片, 而在文末提到:“榮獲斯大林獎金的電影共計:六十八部藝術片, 三十一部文獻片, 四部通俗科學片?!边@里的“文獻片”顯然又是指紀錄片。筆者難以查找文獻電影指故事片的原文表達 (該文與后面引用的《浙江日報》載蘇聯電影部長波爾沙柯夫的同名文章或許具有極大的相關性, 文中提到《列寧在十月》是表述為“監制員羅門曾攝制著名的關于社會主義革命領袖的影片”, 文獻片或許的確是譯者的主觀加工) , 但進行了刪減工作的譯者顯然認為文獻電影這一中文表達是可以指某種故事片, 盡管極為稀少, 而且文獻電影與文獻片或許還有一些微妙的含義差異, 即“文獻電影”指影片的風格, 而“文獻片”則是片種的名稱。
三, 文獻紀錄片術語的出現及其與“紀錄片”概念的錯亂
20世紀40年代后期出現電影與文獻的關聯, 用文獻片與文獻影片來表達與歷史密切關聯的虛構與非虛構電影。在這樣的背景下, “文獻紀錄影片”《中國人民的勝利》誕生了。該片被稱為文獻紀錄片, 或許正是考慮到文獻片也可指故事片, 從而加上了紀錄片的主詞 (80年代還有漢語報道中用“文獻性故事片”的表述15) 。支持該術語出現的原因與蘇聯有關的另一個證據, 是當時中蘇合拍的大型紀錄片是形式雷同的兩部, 其中合作方為蘇聯中央文獻電影制片廠的《中國人民的勝利》使用了文獻紀錄影片標簽, 而與莫斯科高爾基電影制片廠合作的《解放了的中國》卻沒有使用。然而, 在后續的媒體報道中, 《解放了的中國》卻被稱為“文獻片”, 16當然也有與《中國人民的勝利》一起并稱兩部“文獻紀錄電影片”。17還有一種情況, 在談到《中國人民的勝利》為文獻紀錄片時, 稱《解放了的中國》為“藝術片”。18這兩部很少使用資料影片、基本在當時拍攝、甚至大量事后搬演的影片很難說與匯編電影有何關聯。排除罕見的故事片案例, 文獻紀錄片與文獻片仍具同一性, 并且指具有文獻價值或普通人眼中的史料價值以及表現歷史的影片, 實際上也有報道稱這兩部影片為“彩色歷史紀錄片”, 19并歸入紀錄片中, 成為紀錄片中的一類。正如當時文化部長沈雁冰在《中國人民的勝利》攝制完成的晚會上的發言“認為這是全面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勝利的偉大史跡, 也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具有偉大的政治教育意義和高度的藝術水準的五彩紀錄片”。記者則在概述的時候在紀錄片前面添加了文獻的定語:“第一部具有偉大的政治教育意義和高度的藝術水準的五彩文獻紀錄片?!?0
當然, 這僅僅是漢語表達體現出的對紀錄片的一種認識。因為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文獻紀錄片”等同于“文獻片”, 也就等同于俄語中我們通常翻譯為“紀錄片”的那個更常規地應該被翻譯為“文獻電影”的術語, 因此, 文獻紀錄片的術語雖然受蘇聯影響而產生, 但作為一個單獨的紀錄片種類概念化卻與俄語或蘇聯無關。事實上, 這個廠名后來已大量地被“中央文獻紀錄電影制片廠”替代 (當然也有案例翻譯為中央紀錄電影制片廠, 如1957年記錄毛澤東訪問蘇聯的紀錄片《祝賀》片頭標注的蘇聯合作方) 。筆者查到最早在1954年關于文獻紀錄片《阿爾巴尼亞》的報道中提到:“這個影片是由莫斯科中央文獻紀錄電影制片廠和新阿爾巴尼亞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的?!?1最晚則是1959年報道這個“中央文獻紀錄電影制片廠”拍攝我國紀念建國十周年的幾個活動的“新紀錄電影”《在我們兄弟的節日里》, 22那時中蘇決裂已露端倪。當然, 其間也曾出現過一些比較紊亂的廠名表達, 顯示出觀念的迷惑, 如“《中國農民代表團訪蘇經過》是蘇聯文獻電影紀錄片制片廠出品”。23另外還有一個比對, 就是同一篇文章中并列出現的兩個紀錄片廠, 卻分別有著不同的翻譯, 例如“蘇聯莫斯科中央文獻電影制片廠與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阿列山大魯·沙赫亞中央紀錄電影制片廠聯合攝制了彩色藝術紀錄片《和平與友誼》”24 (當然也有同樣翻譯的蘇聯與波蘭文獻電影制片廠等案例) 。因此, 我們可以說, “文獻紀錄片”這個術語等于蘇聯的紀錄片, 但因語言翻譯的歷史錯誤而錯誤地產生, 并形成了一個不同的紀錄片類型。盡管國外也可能有這樣的誤解, 卻沒有相應的語詞表達, 而只是形成一種模糊的認識, 進而隱晦地影響其紀錄電影觀念。
這一論斷我們還可從另一角度加以論證。50年代以后, 報刊上開始有一批蘇聯電影文章被成系統地翻譯出來, 而這些直接譯自蘇聯相關紀錄片的文章, 可能會把紀錄片譯為文獻片乃至文獻或電影文獻, 卻很少譯為文獻紀錄片。換句話說, 全譯文的語境不大可能讓譯者將此概念僅等同于紀錄片中的一個亞類。反之, 在中國對蘇聯東歐電影的報道中卻常常會用文獻片或文獻紀錄片的表達, 而這些表達實質上就是指紀錄片或長紀錄片, 例如筆者曾提到中文報道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上的“文獻紀錄片單元”實際是長紀錄片單元。25實際上, 我們還可從報刊報道中找到諸多文獻紀錄片與短紀錄片或故事片并列的例子, 隱含著其與長紀錄片的等同, 更多的例子還有:“在戰時攝制的十六部藝術片、十二部文獻片、與兩部通俗科學片, 也都已獲得斯大林獎金?!?6文中將蘇聯獲獎影片的種類分為藝術片、文獻片和通俗科學片, 這實際上就是1949年后我國官方的片種分類:故事片、新聞紀錄片和科學教育。在筆者看來這些是袁牧之引自蘇聯, 始于他在東北電影制片廠提出的“七片生產”口號。由于新聞片一般較少出現在電影頒獎的獎項中, 因此這里的“文獻片”實際就是紀錄片。類似的一個被翻譯成文獻紀錄片的例子就不難理解實際上應該還是紀錄片, 僅翻譯不同, 當然這個翻譯是對蘇聯文化部部長米哈伊洛夫《真理報》發表文章的摘譯:“……我們還要同外國電影界共同攝制一些藝術片、科學片和文獻紀錄片?!?7以及新聞報道“協定規定在蘇聯和美國彼此首次上映兩國影片時邀請兩國電影工作者參加, 交換藝術片、文獻紀錄片和科學普及片”。28更有說服力的, 是1959年《人民日報》的一則短訊:“莫斯科訊蘇聯在七年計劃中, 要進一步發展電影事業, 增加各種各樣的影片的產量。單在最近三年中, 就要攝制三百五十部故事片, 二千部以上的文獻紀錄片和科學教育片, 約五千部各種各樣的新聞短片?!?9這個時候, 文獻紀錄片的名稱已在中國普遍化了。上述表述中, “文獻紀錄片”實際上都應該指紀錄片, 但漢語的表達卻只是其中一部分。
四、“文獻紀錄片”的廣泛使用及其類型意識
《中國人民的勝利》等中蘇合拍“文獻紀錄片”及后續的中蘇電影交流對中國紀錄電影形態構成的重大影響不在此贅述。筆者也曾提及, 從《抗美援朝 (第一部) 》開始, 文獻紀錄片在漢語中作為紀錄片中的一個類型被廣泛使用。一個原本是紀錄片的概念被使用為紀錄片中的一種, 那么就表明一種分類認知的錯亂出現了。
首先就是中國人原本認知中的某些紀錄片不能用文獻紀錄片加以表達, 邏輯上也就不具有文獻價值, 從而與紀錄片的概念相悖。筆者曾詳細論述過新聞片。翻開主要的幾部紀錄片史著, 幾乎沒有不把新聞片與紀錄片混為一談的例子, 包括曾在書中對二者進行了區分并對其區別加以論述的單萬里, 在歷史敘述中也大量不分彼此。30這個問題在西方也同樣存在且非常嚴重, 但長期來說在概念上還是相對清楚的。即便把科學片和教學片都歸入紀錄片的克拉考爾, 也在事實電影 (Film of Fact, 邵牧君譯為“紀實影片”筆者認為不是很妥當) 中并列了三種類型, 即新聞片 (Newsreel) , 紀錄片 (Documentary, 含旅行片、科學電影和教學片) , 以及較新出現的種類——關于美術的電影 (Film on Art, 邵牧君譯為“藝術作品紀錄片”同樣不妥, 國內很多學者直接將其引用并被誤導) 。31
袁牧之提出的“七片生產”口號中包含的“新聞紀錄片”, 原意更應該是“新聞片和紀錄片”。他在1941年就曾對紀錄片跟故事片、新聞片做出明確區分并斷言“中國從來沒有過紀錄片”。32那么當蘇式紀錄片出現之際, 被視為“另一種”紀錄片并冠以“文獻”的限定語就順理成章了。人們熟悉的新聞片因此就是另一種紀錄片 (實際上, 袁牧之的觀念中, 紀錄片仍然不過是另一種新聞片而已, 新聞片與紀錄片的關系筆者另文詳細撰述) 。無論如何, 如同文獻紀錄片一樣, “新聞紀錄片”的表達在西方也幾乎沒有, 33而在中國, 隨著官方原本基于工作模式形成的片種分類體系的穩固, 這個術語日益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地視為一個片種。甚至在陳荒煤的多次講話或撰述中, 通篇幾乎都將其作為一個單一的片種。34實際上, 方方的一個表述就將這種思維明確地表達了出來:“……還有人提出‘形象化的政論’是否能概括新聞紀錄電影的特性?因為列寧當時可能僅指新聞片而言, 時代在前進, 藝術也在發展, 這一論述對于多種風格樣式的新聞紀錄片, 特別是其他類型的紀錄片來說已不確切地適用了?!?5《辭海》紀錄片詞條更加明確地表述紀錄片的不同種類:“由于題材和客觀方法不同, 可分為時事報道、文獻、傳記、自然和地理等紀錄片?!?6在《毛澤東文藝思想大辭典》的紀錄片條目中, 則調整為:“根據題材和表現手法的差別, 可分為時事紀錄片、文獻紀錄片和傳記紀錄片、藝術性紀錄片等?!?7
《中國人民的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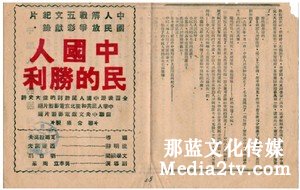
《中國人民的勝利》 下載原圖
換句話說, 文獻紀錄片終于成為紀錄片中的一類, 其代價則是“其他種類”紀錄片的非文獻價值, 因為其標簽就是“具有文獻價值”。其背景則是一些只有“記錄”特點的片種, 特別是新聞片被歸入了紀錄片的范疇, 進而延續出諸多紀錄電影觀念的亂象。
注釋
1 [瑞典]特朗德·倫德莫《電影理論作為檔案理論》, 張泠譯, 《電影藝術》2014年第1期, 第109-113頁。
2 張錦《電影作為檔案》, 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版, 第329-352頁。
3 盡管如此, 筆者并不建議將檔案片看做紀錄片的漢語表達, 因為這個術語最好對應另一個概念, 即存檔電影。筆者查找到最早收入“文獻紀錄片”詞條的漢英詞典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漢英詞典》編寫組編《漢英詞典》,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 第722頁。文獻紀錄片的對應英語表達為“documentary (film) ”, 與紀錄片 (記錄片, 記錄片兒) 詞條幾乎一樣。從這里我們也看到文獻紀錄片在找不到英語的對應表達的時候就等同于紀錄片。此后有文獻紀錄片詞條的漢英詞典雖然不多, 但基本都繼續沿襲。
4 這一定義的漢語翻譯來源于:[法]拉·巴桑、[法]達·索維吉《紀錄電影的起源及演變》, 單萬里譯, 《世界電影》1995年第1期, 第207-232頁。譯者實際譯為“文獻資料價值的或在文獻資料的基礎上”, 后加“資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譯者對“文獻”這種翻譯的某種遲疑。單萬里應是最早在學術上將紀錄片與文獻性建立明確關聯的中國學者之一。本文除非特別指出, 文中的“紀錄片”均指紀錄電影。
5 Barsam, R.M. (1992) .Nonfiction Film:A Critical Hist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75.
6 Leyda, J. (1970) .Films Beget Films:A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Film.London:Hill and Wang.p9.
7 時間《簡論匯編性紀錄片 (文獻紀錄片) 的創作》, 《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7年第11期, 第28頁。
8 區永祥《電影工程第十四部:電教文獻》, 《電影與播音》1943年第5期, 第22-23頁。
9 楊恩榮、范厚、王少明合譯《珍珠港的軍事秘密:本文系金大電專電教一三五“電影文獻”學程教材選譯》, 《電影與播音》1944年第9-10期, 第32-33頁。
10 《影音文獻:金陵大學電影部致該校全體教職員書:我們要用新工具教新材料:這是一個運動!:給本校同仁的一封公開信》, 《電影與播音》1946年第8-9期, 第54-55頁。
11 《中國第一部文獻片》, 《戲世界》1947年第312期, 第9頁。
12 《1947蘇聯五一節大檢閱》, 《申報》1948年5月11日。
13 沈江《蘇聯文化近影》, 《人民日報》1949年5月23日。
14 伊凡諾夫《蘇聯電影三十年》, 《大公報 (上海版) 》1949年12月25日。
15 楊《〈西安事變〉將拍成文獻性故事片》, 《電影評介》1980年第6期, 第28頁。
16 [蘇]C·格拉西莫夫《兩大民族間的不朽友誼》, 《人民日報》1951年2月15日。
17 錢俊瑞《世界和平的萬里長城慶祝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一周年》, 《人民日報》1951年2月13日。
18 《〈解放了的中國〉及〈中國人民的勝利〉兩影片榮獲斯大林獎金一等獎》, 《人民日報》1951年3月21日日。
19 新華社《蘇聯電影工作者幫助我電影事業迅速發展》, 《人民日報》1951年2月18日。
20 本報訊《中蘇電影工作者合作五彩巨片〈中國人民的勝利〉攝制完成》, 《人民日報》1950年9月25日。
21 《慶祝阿爾巴尼亞解放十周年首都各界舉行慶祝大會》, 《人民日報》1954年11月29日。
22 《紀錄慶祝我建國十周年盛況蘇聯攝成兩部新片》, 《人民日報》1959年10月26日。
23 《蘇聯影片展覽增加特別節目》, 《浙江日報》1952年11月16日。
24 曉風《蘇聯與羅馬尼亞聯合攝制彩色紀錄片〈和平與友誼〉》, 《世界電影》1954年第4期, 第90-91期。
25 引證的實例來自《第七屆國際電影節舉行授獎典禮我影片“人民的戰士”獲“爭取自由斗爭獎”》, 《人民日報》1952年8月6日;克勤《紀錄著越南人民斗爭的影片》, 《世界知識》1952年第34期, 第15-16頁。
26 [蘇]波爾沙柯夫《蘇聯電影三十年》, 《浙江日報》1950年3月11日。
27 《蘇聯大力發展同各國的文化聯系》, 《人民日報》1957年2月20日日。
28 《促進相互諒解的重要步驟蘇美兩國簽訂文化交流協定》, 《人民日報》1958年1月30日。
29 國際簡訊《蘇聯在三年中將攝制大量影片》, 《人民日報》1959年3月11日。
30 單萬里《中國紀錄電影史》,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年版, 第303-305頁。
31 Kracauer, Siegfried.Theory of Film:The Redem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p193, 中文翻譯版為:[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現實的復原》, 邵牧君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年版, 第244頁。
32 殷參《袁牧之帶著攝影機從敵人后方來:大談紀錄電影與邊區劇運》, 《中國電影》1941年第2期, 第49-53頁。
33 在中文工具書中, 新聞紀錄片詞條幾乎都明確是新聞片與紀錄片的統稱, 而漢英詞典中筆者找到的最早也是唯一的詞條是:潘紹中《新時代漢英大詞典》,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 其對應英語表達為“a documentary film, a news documentary”。埃里克·巴爾諾 (Erik Barnouw) 曾在《紀錄片:非虛構電影史》 (Documentary:A History of the Non-Fiction Film, 2nd ed.) (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中曾使用過journalistic documentary一詞 (p67) , 中譯本譯為“新聞紀錄片” (《世界紀錄電影史》, 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2年版, 第64頁) 亦可但不妥。這里更主要表達新聞片與紀錄片制作合一環境中的紀錄片 (《電影作為檔案》中有過詳細分析) , 因為前文提到“作為紀錄片制作者的記者”, 且基于新聞片的匯編影片即我們眼中與新聞紀錄片對立的文獻紀錄片也屬此類。該詞或譯成“新聞記者 (新聞業) 的紀錄片”或“報道式紀錄片”, 但這種表達也不多。
34 陳荒煤《加強新聞紀錄電影工作的黨性》, 《電影藝術》1960年第4期, 第12-21頁;荒煤《代序:向縱深發展攀登新的高峰》, 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第1-5頁。
35 方方《中國紀錄片發展史》,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版, 第206頁。
36 轉引自倪祥?!兑舱摷o錄電影的起源──與聶欣如同志商榷》, 《電影藝術》1999年第3期, 第89頁。
37 馮貴民、高金華主編《毛澤東文藝思想大辭典》, 武漢: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 第340-341頁。





 客服1
客服1